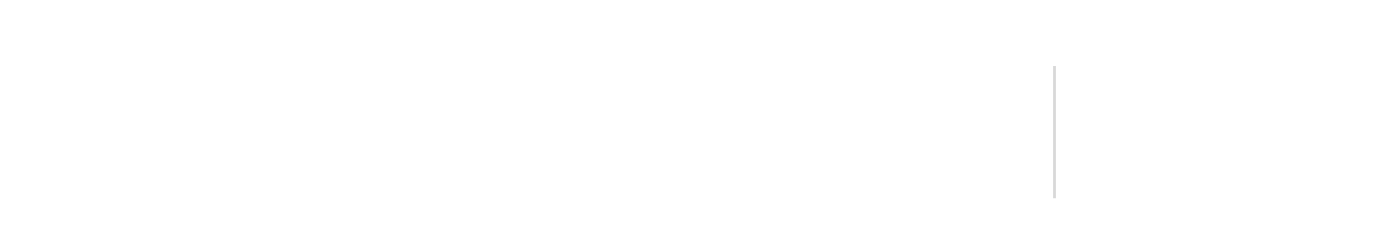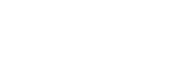问诊“大城市病”
时间:2015-12-17
作者:中国城市报 编辑:张佳宁 浏览次数:

编者按
城市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聚集空间,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特大城市成为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要基地。然而,人口畸形集中、住宅紧张、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城市病”逐渐凸显,破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制约城市健康发展和城镇化的可持续推进,为城市治理带来了不小挑战。对此,来自政、产、学、研各界多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对当下特大城市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供真知灼见。
病症一:人口暴增
近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公布。其中关于调节北京市人口结构的内容引起了关注。
根据《建议》的目标,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左右,“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缓解,首都核心功能显著增强。
然而北京人口规模调控的形势依然严峻。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为2151.6万人,其中城六区常住人口达1276.3万人,但人口规模还处在增长状态。“十三五”期间想要实现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左右,这也就意味着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和石景山的人口将疏解近200万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段霞指出,虽然北京现在要在2020年把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但是指的依然是统计人口。“加上我们现在的移动人口,加上公安局统计的是将近800万,再加上其他短期过境人口,在北京应该是超过1000万以上的人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流动人口,他们大量的向大都市聚集。”段霞说。
被列为一线城市的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大城市病”与人口问题同样存在。上海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左学金表示,上海从2000年-2010年,常住人口增长了694万,将近600万(598万)是非户籍人口的增长。
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资金流、人流、物流等回报率高于中小城市,造成许多人口向大城市转移。有学者认为,人口规模不应成为特大城市发展的目标。无论是“人才”还是“人口”,都是城市发展的财富而非包袱。行政手段控制人口有悖于公平,也损失效率。
对此左学金表示赞同。“行政控制人口不是一个好办法,我们已经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劳动力,这个如果不是市场配置,决定性作用很难体现。实际上行政控制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造成劳动力人才资源配置的效率比较低,人口不能流动,保护主义要求越来越高。”左学金说。
特大城市作为我们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在“十三五”时期,如何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缩小人口规模,是建设和发展特大城市中所要重视的一大问题。
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副会长李义虎提出需要以创新驱动新经济。他表示,只有发展以新技术革命为龙头,具有知识资本密集型和低污染、低耗能的新经济,才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缩减现有的人口规模,进而缓解特大城市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和交通等等问题。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区域一体化也成为疏散北京人口问题的出口。目前,北京与天津、河北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和合作方案化解“大城市病”,塑城市新功能。
病症二:交通拥堵
日前,北京市交通委透露,2016年将研究试点征收拥堵费,并针对小客车、机动车实施更加严格的限行措施。通过立法方式确定如何收费,并将收取拥堵费纳入《北京市缓解交通拥堵总体方案(2016-2020年)》。消息一出,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堵”已成为特大城市的不二标签。近年来,中国汽车的保有量呈野蛮式增长,城市交通问题日益凸显。根据高德地图报告,今年第二季度,国内十大堵城依次为北京、杭州、广州、济南、大连、哈尔滨、深圳、上海、重庆、成都。位居榜首的北京高峰拥堵延时指数2.10,意味着高峰出行是畅通下花费时间的2.1倍。
相关数据显示,北京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比例仅为48%,与国内外主要城市还存在明显差距,而机动车每车的年均行驶里程却是伦敦的1.5倍、东京的2倍。
虽然近些年,在如何解“堵城”之困上,北京市进行了单双号限行、错峰上下班、加快公共交通建设等诸多尝试,但是效果不是十分明显,一旦遇到节假日或恶劣天气,堵车现象尤为严重。
然而拥堵不是简单的道路、机动车保有量、管理等单一方面原因造成的,而是多年以来多种原因形成的“慢性病”。
来自英国《经济学人》的一组数据指出,影响吸引投资的众多因素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交通,占比达27%,而第二、第三位的安全、教育,占比仅为9%和6%。而在环境后果上,一个特大城市因交通拥堵每天多排放的二氧化碳,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导致环境损失45亿元。
目前特大城市规划中所应用的功能分区理念,在上海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左学金看来,也是造成拥堵的根源之一。“现在特大城市旧城改造,把大量的中心城市人口搬迁,我们看报道,北京五环以外住的人口占了55%,中心城区都是商务楼,看起来中心城区常住人口下降了,但是就业人口大量增加,就业人口住在城乡结合部,这样造成大规模上下班通勤的交通。”
对此左学金建议,对于多中心空间布局,应在各自主体功能的基础上,引导多样化的非主体功能,避免过于单一的功能结构布局;引导产业合理布局,缓解职住分离的状况。
针对拥堵问题,左学金还提出建设“紧凑型”城市。
“大家很担心,如果密度提高会不会拥挤?我可以说拥挤是低密度城市的特征,不是高密度城市的特征。我们常常认为密度高了就要拥挤,交通拥挤不是人多是车多,为什么车多呢?因为要开私家车,为什么要开私家车,因为密度太低了。如果密度高,就减少了对私家车的依赖,可以更多的运用公交,反而交通不拥堵。”左学金解释说。
病症三:环境恶化 资源短缺
12月10日,北京进入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第三天。据预报,伴随冷空气入境,午后,北京市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将出现好转,12时后,重污染红色预警将解除。这是北京自2013年《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通过以来,首次启动红色预警。市民们纷纷调侃:面对“十面霾伏”,除了“自强不吸”外就只剩等风来。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中国11个特大城市中,每年因大气粉尘造成的死亡人数多达 50万,40万人患上慢性支气管炎。
除了空气污染外,水资源短缺也成为制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记者查阅相关数据了解到,2010年末,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仅约为100立方米,不足纽约、巴黎、东京的1/20,每年缺水10亿立方米。北京市每天产生1.84万吨垃圾,产生量每年还在以 8%的速度递增,而全市垃圾设计处理能力尚不及垃圾产生量的70%。
前不久,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目标和“绿色”发展理念。
专家和学者纷纷表示,上述目标和理念要求,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高,能源和水资源消耗等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叶耀先表示,“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曾认为,经济搞好了,社会、生态都会好,实际上不是这种情况,经济搞好了,社会和生态没有好,所以开始就要注意生态的问题。经济是社会的指针,社会很多重要的方面并不包含在经济里面,而且人类社会在总体上受地球自然的生态制约,所以生态要融入经济社会。”
叶耀先还指出,特大城市发展要追求的可持续要体现三个“最”:第一个是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第二个是环境影响最小,第三个是对生物种群最好。
“要设法留下大自然的地表,不要用人造物把整个大地覆盖,现在整个城市洪涝灾害,像“海绵城市”最关键的问题是地表透水性不行了,而且现在又强调地下空间的使用,我觉得地下空间要合适使用,不能都使用,现在有很多小区地下都挖空了。像台湾有一个绿色建筑叫“基地保水”,基地的水还要保持,比如像这样的问题就是生态问题。再比如,城市中心有一个小的生态区域,不要搞花盆式的大自然。另外,建造生态系统各个因素整合的城市,不要搞与周围大自然隔离的机械城市等等,生态城市的做法很多,我们要向这方努力。”叶耀先说。
首经贸新闻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①凡本网未注明其他出处的作品,版权均属于首经贸新闻中心,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首经贸新闻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责任。 ② 凡本网注明其他来源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对其负责。 ③ 有关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与本网联系。 ※ 联系方式:首经贸新闻中心 Email:xcb@cueb.edu.cn
最新新闻
学校要闻